
【财新网】(记者 黄姝伦 汪苏 实习记者 樊朔)乡村“空心化”、衰败不堪,近年来成为广为关注的社会现象。不过,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表示,在当下中国,人不断地汹涌地往村庄外跑,而且是一去不复返地跑,是到农二代以后的现象,这代人离土、出村、不回村,加剧了整个村庄普遍的破败,有的地方死寂一样地没有希望,这是不正常的。
“人类社会的现代化,不是以乡村衰败作为前提的。城市化也不是以乡村衰败为结果的。”日前,刘守英在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演讲时表示。
他认为,我们一方面要研究整个大趋势,就是70、80、90后的迁移现象,他们对土地的观念、对农业的依靠、与村庄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,但是也要找出不正常的原因。其中的因素可能有:首先,单向城市化思维,形成城乡不平等的发展理念,乡村没有合法平等参与城市化、工业化的权利。比如,农村就是搞农业,农民的宅基地就是居住;第二,是城乡收入机会的差异。人们出去打工,两个月赚的比农村一年的收入要强;第三,乡村衰因农业窄而起。
“很多人去台湾、去日本学,没有见到乡村是这种情况。乡村会缩但是不会败。乡村要活,农业要活,否则乡村赖以生存的产业就没办法和城市竞争。我们的问题在于农业越来越窄。”刘守英说,就是到现在,农业为城市提供粮食的基本功能没变,这导致农业越来越窄,农业获利有限,“你怎么指望农民就守着那一亩三分地?于是农村就越来越衰败”。
刘守英表示,农二代与农一代的代际差异,正在给农村带来深刻变迁,引爆乡村经济革命。与农一代比较,这一代人呈现出一些具有“革命性”的特征,一是离开土地,不知道自己的地在哪;二是不再以地为生、以农为业;三是夫妻出去、举家迁移比例提高;四是回乡不回村,春节回家乡开车回去,回到县城,住在县城;五是买房不盖房。第一代农民工的特点是出去挣钱,然后把钱寄回来。现在的农民不回村盖房,人走资本不回;六是孩子的教育能到县城的就到县城,不行就到乡镇。
“我们不反对城市化的这个趋势,但是乡村的未来不是简单靠城市化就能解决的,需要重新审视城乡关系。”刘守英表示。
他认为,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是被无视的,“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功夫,但到现在来说,还是一头围绕农业和农民增收,另一头围绕要素怎么快速地配置到城市,乡村本身如何现代化,这是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的。”
刘守英还表示,中国乡村的不正常之处还在于,人走后,大部分村庄是“衰而未亡”。由于现行宅基地制度等原因,村庄“死不了,也活不好”。
不要泛找“乡愁”
面对衰败的乡村,怎么办?
乡村破败,引起了很多“乡愁似”纪念。有的人甚至喊起反对城市化的口号。刘守英则称,“不要故作忧虑,也不要矫情地去找乡愁,这两个都是非常要命的东西。”
过去一年,刘守英跑了贵州、青海、西藏、甘肃以及浙江、安徽、上海、江苏等多个地方,观察乡村现状和实践。“走下来对乡村整体的感觉是越来越有眉目了。与过去乡村的苦与无望相比,农村整体状况在向好。这个是要客观的。”
他表示,一些人忧虑的东西已经是趋势性的,“忧虑是没有用的,这是规律。另外我觉得找乡愁也是很可怕的,很多知识分子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找乡愁,问题是现在的乡村是愁不来的,有些人只是从局外人在看乡村,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矫情。”
他认为,大部分乡村的“衰而未亡”和部分村庄的活化,是城乡中国阶段的重要特征。“这个我们可能要扛个几十年”,而衰而未亡和活化的部分都是由城市需求产生的。
同时,“绿水青山在很多地方就是绿水青山,只有部分地方有条件变成金山银山,你看到一些地方是绿水青山,不要人为总想着把它变成金山银山。”刘守英表示,条件不具备的地方,是变不成的,一些地方人为地去打造,可能是会变出一些问题的。
不过,刘守英看见,在一些地方,有产业生命力、能带给村庄活力和未来的东西,已经生长出来。带来这些改变的举措包括:人退绿进、土地改革、调整粮经比、发展区域特色农业等等。
比如,贵州湄潭,1987年率先试验农地“增人不增地、减人不减地”,即不再随这人口增减重新分配土地。新增人口怎么办?一条路是荒山拍卖,向荒山要活路。
他表示,30年来,湄潭农村形成了改革的氛围,撬动了发展。以60万亩荒山为基础,湄潭发展了支柱性的茶产业。“茶带动的相关产业一年可以搞到88个亿,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——农业工业化。在荒山开发的基础上,把生产要素重新组合起来,从规模化种植到品牌化销售,形成了全国最大的绿茶市场。”
刘守英表示,农村形成了一条产业链条后,乡村就有看头了。加之湄潭温度适宜,夏季非常凉快,“通过产业延伸,这里的旅游业和服务业也发展得非常好。”
又比如,贵州省安顺市近年发展出“金刺梨”产业。粮经比(编者注:“粮经比”指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之比)的调整,对整个地区乡村发展机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。整个安顺的粮经比从52︰48调整到30︰70。目前,安顺种植着几十万亩的“金刺梨”。当地逐步发展起了中药材、精品水果及农产品加工等山地特色农业。
公共政策应着眼于哪些活和如何活
刘守英表示,乡村“衰而未亡”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公共政策放在哪些活和如何活上,这里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的。
首先,要重新思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。未来中国将会进入到这两个文明都开始有自信、有平等发展机会的阶段。城市文明是离不开乡村文明的,“就像我们城里人,在城市待久了,是需要换空气、换心情的”。而乡村文明也是离不开城市文明的,“未来我们公共政策的重点,应该把这两个文明当做平等的、共存的、共荣的文明来对待。这是我感受最深的。”
第二,要思考由代际革命引发的乡村现代化。首先,一个基本判断是乡村一定要现代化。农业、农民、农村的现代化对整个现代化的作用是需要补课的。没有农村的现代化,整个现代化是不可持续的。这是农村现代化和全局现代化之间的关系。
再者,这一轮农村现代化的独特性在于不是简单的乡村复古,也不是简单的乡村现代,它的重点在于代际革命的概念。农二代、农三代对乡村的观念、与乡村的关系、与土地的关系,可能会决定我们整个乡村现代化的走向。
第三,整个村庄的转型必须由宅基地改革作为牵引。村庄要动,无论死也好,活也好,需要有一个东西来撬动,“只靠财政制度,只靠特殊的优惠,村庄是活不了的”。未来村庄转型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宅基地改革一定要有突破。宅基地突破后,村庄才能“该死的死,该活的活”。
刘守英表示,目前整个宅基地制度就是让村庄“衰而未亡”,死不了,也活不好。宅基地基本上是以成员权为基础无偿分配,“结果就是不要白不要,农民并不在村庄但是还在占着这个东西,这样的村庄就不可能死”。而在“村庄的活”中,宅基地也可以起很大作用。现在这种成员权的身份制度,将村庄封闭起来。要让宅基地真正作为一种财产权,里面的人可以走,外面的人可以进来。“这个怎么往前突,现在需要进一步的制度设计”。
第四,村庄的变化跟整个农业制度的变化积极相关,整个农地权利如何设置,经营制度如何设计,来推动整个农业的转型,也非常重要。■




 北汉前边庄阳光
北汉前边庄阳光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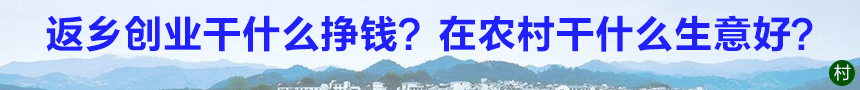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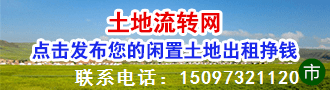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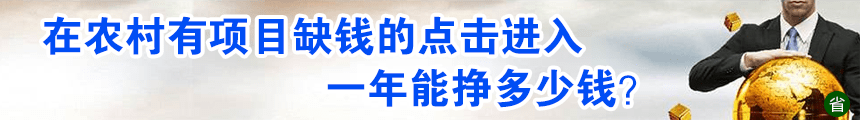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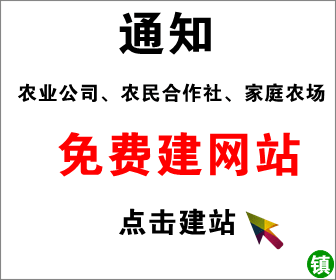
 苏ICP备18063654号-3
苏ICP备18063654号-3 苏公网安备 32011202000276号
苏公网安备 32011202000276号

